蓝朝云,瑶族,笔名:云豹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人。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是世界文学艺术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散文集《家》《春》、短篇小说集《天桥》、中篇小说集《山里人》《瑶山春》、长篇小说《红绒线》《山弩神威》、叙事长诗《喜鹊之歌》第一部《浴火神侣》和第二部《双雄神剑》等作品,写过《红绒线》等多部电影剧本。散文:《理念坚定了我上大学的决心》收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瑶族卷》。
最新文章
-
共叙健康之美 共筑友谊之桥 京城
1天前
共叙健康之美 共筑友谊之桥 京城俱乐部巴西节庆日庆祝活动纪实
【详细】 -
2025-09-09
-
2025-09-08
-
2025-09-08
-
2025-09-08
-
2025-09-08
瑶族爱情叙事长诗《喜鹊之歌》第二部欣赏
来源:世界经济合作网
|
作者:世界经济合作网
|
发布时间: 2024-04-19
|
1031 次浏览
|
分享到:
蓝朝云,瑶族,笔名:云豹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人。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是世界文学艺术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散文集《家》《春》、短篇小说集《天桥》、中篇小说集《山里人》《瑶山春》、长篇小说《红绒线》《山弩神威》、叙事长诗《喜鹊之歌》第一部《浴火神侣》和第二部《双雄神剑》等作品,写过《红绒线》等多部电影剧本。散文:《理念坚定了我上大学的决心》收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瑶族卷》。
瑶族爱情叙事长诗《喜鹊之歌》第二部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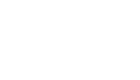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作 者 简 介







世界文协小说二部部长蓝朝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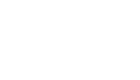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序
蓝克宽
近期,蓝朝云送来他辍笔不久的《喜鹊之歌》第二部《双雄神剑》的稿子让我看,并恳请写序,我回想阅读第一部《浴火神侣》留下的深刻印象,便情不自禁地答应了。
早在二十多年前,壮族著名诗人韦其麟大师在他的长诗《百鸟衣》再版的《前记》中写到:“《百鸟衣》是根据壮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1955年6月在《长江文艺》发表,接着《人民文学》和《新华月报》分别转载。”“我写长诗时,吸取了民间故事的基本情节,但对主人公的身世、成长过程和结尾等都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作了改造和补充,也删去了原故事一些我认为不太合理、不够理想的情节。”(见韦其麟著《百鸟衣》再版《前记》,漓江出版社1998年9月版)。读罢朝云同志的《喜鹊之歌》第二部《双雄神剑》,我认为,此长诗是根据他多年田野采风收集到的布努瑶民间故事创作,而不是搜集、翻译、整理的民间叙事长诗。
《双雄神剑》是继《浴火神侣》之后,描写主人翁敢松与珍凤凄美爱恋故事的续篇。他们刻骨铭心、催人泪下、追求自由的爱情贯穿全书,悲欢兼有。但两人的爱情不是整日的卿卿我我、如胶似漆或哀怨忧伤、涕落衫巾,而是与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为了黎民百姓能祛灾脱难,获得幸福,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斗志昂扬,赴汤滔火,相互激励,奋勇前行,读来令人唏嘘、赞叹不已。
我曾多次阅读这两部姐妹长诗,掩卷之后常自语:作者对人物
塑造、故事情节、场面景物等描写惟肖惟妙,逼真如实,活灵活现,可以说,创作很成功,是布努瑶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宝。
首先,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进行文字的艺术加工,匠心织就二十三篇感人的故事。
长诗的每篇故事都色彩纷呈,情节跌宕起伏,如大江长河,前波未止后浪至,波波相接,惊心动魄,且各唱段之间的悬念不穷,引人入胜。不是吗?时值布努瑶山地一妖魔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伤人吃肉,并散布霍乱,导致尸骨成堆,哀鸿遍野。符华先·法华凤和密洛陀让主人翁敢松和珍凤的魂灵变为人样,一路杀妖魔鬼怪和虎豹豺狼,历尽艰辛,终于登上弥兰山,取回多功能神剑。这些壮举可歌可泣,让人阅后难于忘怀。
其次,参照古今汉语诗歌的押韵妙招作词。
凡是唱词,都参照汉语诗歌的押韵规则,双句押韵,通顺易懂,实为难得。
这种押韵妙招表明:作者造句作诗时,将布努瑶用语习惯和汉语诗歌的规律交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化目的。”(费孝通著《中华文化的重建》第29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最后,各唱段的开头和结尾皆“过门”。
何谓“过门”?即歌唱者在每一段唱词开始时,常用承上启下的调子唱“耶—呃——哦—,麻尼勒—先喔喔”(此为布努瑶古语,意思为“故事是这样的”或“开始啦”)。
结尾用“麻尼勒—先喔喔”(这也是布努瑶古语,有“我唱到此,你可以接着唱”或“有什么问题或疑问请提出来”的意思)。
这种“过门”词,类似于汉语歌词中的“衬词”,“是中国民歌语言表现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有着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力。对表达思想感情,增强生活气息,渲染某种气氛,显示地方风格,丰富音乐表现手法等起了一定的作用。”(余铨著《歌词创作简论》第12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版。)
综上可知:长诗《喜鹊之歌》第二部《双雄神剑》已形成一个光环:既有布努瑶的民族特色,更有布努瑶的语言特点,它的出版,可喜可贺。
顺笔至此,我想起全国著名教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陶立璠先生在朝云同志的长诗《喜鹊之歌》第一部《浴火神侣》写的序中的点赞:弹指30多年过去了,蓝朝云“终于把《喜鹊之歌》(第一部《浴火神侣》)以诗歌的形式创作出来。用心良苦,实是为了延续布努瑶民间文学的文脉,使其代代传承。从这个角度看,同样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可以说,这是对瑶族文化的贡献。”当代著名大作家蓝怀昌在序二中兴高采烈地说到:蓝朝云“在创作《喜鹊之歌》(第一部《浴火神侣》)的过程中,始终把爱当作精神世界的唯一永恒,因此,作品保持了传统叙事诗的结构框架,保持了布努瑶的语言特色,在细节上大胆加工,诗句上不断润色、提升,使整部长诗的语言含蓄、凝练,增强了可读性。从整体上看,作者的创作是成功的,是布努瑶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这话用作《双雄神剑》的赞语亦不为过,恰到好处。
勿庸讳言,我写的这篇序言纯属受到上述两位大师的金玉良言的开导,荣幸之至哉。
我可以推定:待到第三部《史传神棍》问世,整部《喜鹊之歌》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二部《百鸟衣》。正是:相距六十六年诞生的两部长诗,“像天上两颗星星,永远在一起闪耀。
”二〇二一年7月8日于南宁半山丽园阿鸾书屋。







《喜鹊之歌》第二部《双雄神剑》主要故事梗概
布努地区有一妖魔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残吃人肉,并散布霍乱,造成遍地洪水泛滥,尸骨成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布努圣祖符华先•法华凤和密洛陀让敢松、珍凤的魂灵幻变为人样,派他们去弥兰山取双雄神器。俩恋侣历尽千辛万苦,一路杀妖魔鬼怪和虎豹豺狼,战胜种种困难,终于登上弥兰山,取回多功能的宝物(一把神剑,一根神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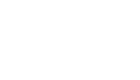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喜鹊之歌》
第二部《双雄神剑》
节选之一
永生
男引唱:
说奇不怪自然事,
应验显灵破天荒,
叭叭几声如强震,
刑场旁边突爆响,
坚硬石板露长痕,
指头裂口扩成塘。
坑内喷泉高数丈,
纷纷扬扬似雾霜,
清澈见底翻涟漪,
冲击塘边似涌浪,
众人围观瞪直眼,
言语不得皆惊惶。
吸溜几声水消尽,
瞬间变化谁能挡?
底层残留鸡鸭毛,
疑是河水破谷滂,
面面相觑身寒战,
装聋作哑心胸慌。
焰火熊熊势更猛,
哔啵之声荡空旷,
浓烟滚滚升半空,
搅成雾团云微烫。
生死恋人歌再起,
语气凄婉且高昂,
曲调悲凉词凄愤,
多数观者泪满眶,
默默无语低下头,
似是鞠躬来悼伤。
烈火烧不熔肝肺,
毁不断爱恨情长,
赴难之时无畏惧,
微微一笑互对望,
颔首互道祝福语,
无哀无痛赴仙堂,
俊美容颜得永生,
流芳百世耀辉煌。
敢松珍凤合唱:
有幸相遇爱今生,
风雨摇曳雷霆响,
霸主举鞭舞刀棒,
不能结合去腾扬,
发不同青心同热,
生不同衾死同辌①。
今日含恨共赴难,
约定百年转山乡,
涅槃重生走二次,
现身人间披婚装。
生儿育女膝边跑,
孝敬双亲享寿长,
山边放羊地种黍,
桃李树下看翠篁,
箫引凤凰与喜鹊,
伴随我俩度艳阳。
敢松:
再见了心肝人儿,
永别了我的新娘。
珍凤:
再见了心上人儿,
永别了我的新郎。
女引唱:
两只喜鹊火中起,
扑棱翅膀相依偎,
绕场几圈泣同声,
再忆人间恨与爱,
穿梭往来渐飞高,
众人叹息多嘘唏。
相爱之人化为鹊,
振翅拍膀向西去,
飞越高山过峻岭,
惊起禽类千万只,
白鹭大雁与百灵,
画眉杜鹃和燕子,
先后展翼出草窝,
哀怨共鸣来跟随,
前后左右与上下,
东西南北音各异,
护卫双鹊翩翩去,
如同姐妹与兄弟
遮得大地处处暗,
胆战心惊人人骇,
五指不见路难认,
世间稀有此怪事。
——————
1、辌:古代可做床睡觉,
也可以平放死人的丧车。
女引唱:
鸟群刚去暴雨到,
倾盆而下兜头淋,
天河决口万山浮,
水冲地裂千峰移。
山洪咆哮坡体塌,
犹如万马驰骋急,
摧枯拉朽泥沙去,
无边树倒竹折碎。
场上民众呼不已,
四处奔逃哪顾及,
狂风雷电助雨阵,
一个时辰才停息。
愣头青儿大着胆,
爬上高台眼惊呆,
两根倚桩焦如炭,
似断未断仍伫立,
绑绳灰烬依稀见,
骷髅骨头无影迹。
彷徨许久满腹疑,
抬头看天雾迷离,
低头试问各巫师,
摇头晃脑均装痴。
男引唱:
旁观老者独叹息,
垂头坐地身披霜,
沉思良久捋髭须,
伤心掉泪出口唱:
敢松珍凤化仙去,
人成牲品世肮脏,
姨娘梅英跟随后,
罗立鼓锣启宫阊。
愤恨难消冤屈死,
世间不公谁亮嗓?
四股青烟轻飘去,
留得哀怨任评赏。
喜鹊枝头筑巢窟,
和鸣共宿双翱翔,
好过噪杂众人世,
生存自主无尘网。
但愿人间少龌龊,
除尽雾瘴现艳阳,
平等相处去污浊,
日月高照世代昌。







喜 鹊 之 歌
第二部《双雄神剑》
节选之二
受 命
密洛陀:
你们受罪我慢待,
过分谴责心不安,
请予原谅消隔阂,
携手迈步展笑颜。
父亲①话中已点题,
我就直说亮困难:
不知何时下界乱,
魔鬼肆虐特凶残,
来则暴风袭大地,
瘟疫随播多霍乱,
吞噬妇婴极贪婪,
哀嚎声声遍山川,
为非作歹色为餐,
涂炭生灵任剐剜,
虎豹闻之躲僻处,
深藏岩洞气止喘。
去时大雨倾盆下,
洪涝漫野浩无边,
水流不通棚房倒,
存活民众爬峰巅。
华夏南部灾最甚,
死尸漂浮鱼虾啖。
消息传来惊不已,
张口结舌增怒厌,
派出孩们去侦探,
反复多次才揭帘:
群体妖怪住深山,
绵延千里雾弥漫,
————————
注释:
父亲:密洛陀是
符华先·法华凤造
的女神之一,故称。
终日笼罩阴沉沉,
灰蒙一片难见天,
瘴气蒸腾水冰冷,
毒虫蠕动四处钻。
仙体灵神无法进,
远而避之散如烟,
卡亨移走几座山,
导致病菌广扩散,
耕杲念咒挥符旗,
神界兵勇齐出战,
魔头启嘴喷火龙,
山山弄弄皆烈焰,
自顾不暇逃夭夭,
烧伤无数身抖颤。
罗班劈山开河道,
魔头寻机多捣蛋,
飞身银河破岸堤,
水顺决口泄满天,
连续暴雨半个月,
淹没坡梁灾成片,
只好罢手息兵戎,
减少危害求偏安。
凡间有座弥兰山,
高约千仞耸云端,
连接昆仑自成体,
遥遥对望各显艳,
南面林木四季青,
北坡冰封尽荒原,
终年不化白皑皑,
凹凸如镜百里灿。
雾岚缭绕缠中腰,
神秘莫测难攀援,
峰顶分界汇合处,
铁制盒子插其间,
长约丈余呈扁形,
外壳灰色耀目眩,
那是卡亨撬岭棍,
铜心钢体表青绚。
我派老鹰看地方,
飞临弥兰站山巅,
卡亨与之生口角,
互不相让即骂怨,
弃棍在地抓老鹰,
关进黑牢设篱樊,
雪坡坍塌被覆盖,
过后欲拿寻不见。
岁月如梭几千年,
坚冰摩挲成美琰,
琰汁滋润渐膨大,
挤压运动出地面,
裂变为二无锈斑,
剑棍合一相并兼,
公母紧依头尾齐,
柄端镶玉雕龙蟠,
平时潜埋硬石中,
痕迹难显供外观,
偶尔露容闪金星,
光芒四射日夜炫。
竖起高约十丈余,
晶亮透明色天蓝,
净重千斤难挪移,
默诵谶语随心变,
根据需要可大小,
伸缩自由任长短,
亦能化剑利无比,
削铁如泥破峰峦。
卡亨等人独善身,
不怀杂陈抛爱念,
妻儿全无去参拜,
想尽办法几轮番,
均不奏效自长叹,
如此尴尬几百年。
你俩记名在仙堂,
却未除尽前世缘,
心心相印思专一,
眷恋意识仍存焉。
妖魔欺鬼怕生灵,
遇上人气即畏颤,
特派你们去取回,
普救众生脱恶险,
抛却私情办大事,
克制欲望图宏愿,
洁身自爱走正道,
借助东风谱新篇。
如若不听忠告语,
所授符法自消烟,
无地容身成骷髅,
万劫难复沉深渊。
脑子聪颖是你们,
一点即悟知褒贬,
牺牲小我为大局,
如玉生辉世代瞻。
安心去吧俩孩子,
老天保佑胆志坚,
全力以赴渡川江,
披荆斩棘跨沟涧。
走完仙界到凡间,
战胜困苦克万艰,
诚心定会达目的,
登上雪峰凯歌旋。
这里有张路线图,
大致方向可借鉴,
照此直走少费劲,
避开曲道抢时间。
操作规程须谨记,
别当儿戏视为闲,
登上山顶细观察,
化冰洗手净容颜,
点燃烛香洒清酒,
跪地三拜许誓言,
男女分别诵符法,
从头至尾咏两遍,
运气出掌送热量,
溶化薄冰见盒栓,
中间部位击五下,
硬石裂开形体现,
扶住慢挪揿暗键,
自然弹开成两剑,
提拿困难佩不得,
再念符经轻如鞭,
降魔灭妖依靠它,
一切祸害能除歼,
待到魍魉戡灭净,
才许你们合卺圆。
珍凤:
我和郎君相爱恋,
高尚纯洁无肮脏,
却受千般苦与难,
伤痕累累尽祸殃,
魂魄虽存原体毁,
是人是鬼实难讲。
今在崖头树彩旗,
风吹猎猎藏匕芒,
挺胸而上是傻瓜,
粉身碎骨定喂狼。
明知路途多险恶,
偏要我俩去前方,
虎嘴拔牙理髭须,
岂有生还不死亡?
多次刁难设障碍,
威逼利诱推井隍,
暗中害人布深渊,
大言不惭实比糠。
活着最怕遭蒙骗,
自投罗网多凄凉,
尤以亲人背后剑,
刺破髓骨更难忘,
心绞痛兮欲昏厥,
万箭穿胸断肝肠。
今日落难如此惨,
雪上加霜又何妨?
因此勿谈取剑事,
磨刀快来铡喉腔,
愿与情人同时殁,
双双依偎赴墓房,
化作尘埃得黏连,
除却相思免悲怆。
敢松:
罗立受辱刚半日,
记忆犹新魂魄惊,
泣血恳求视不见,
无动于衷多冰冷,
我变蛇蟒透心寒,
孤苦无助欲癫疯,
腿沉如铅移步难,
仍挥帚把扫出境,
刀捅胸腔裂肾脏,
天旋地转向不明。
足落圣地气未消,
又来设骗挂风筝,
绳断翼折落火塘,
纸鸢为灰方清静?
编出事由说种种,
赶尽杀绝才罢声?
雷霆电闪舞银剑,
遍体鳞伤添严惩,
千般箭矢穿骨髓,
万径黑暗遇狰狞,
沼泽遍布铁蒺藜,
阴险毒辣再撒钉,
如此手段世少有,
暂不考虑赴火坑。
男引唱:
唱词激愤显锋芒,
密本洛西陡生气,
脸色铁青嘴歪斜,
欲怒发声却理亏,
强抑盛火举双眼,
倚墙站立望窗外。
鼻祖仙翁看透彻,
柔缓出言劝止息,
各人心思可理解,
关爱有方莫性急,
劝慰双方识大体,
小事化了共对敌。
开口念符显下界,
种种灾情叠影来:
妖魔横行胜虎豹,
屠戮民众似杀鸡,
洪水暴发浪滔滔,
一片汪洋连天际,
山崩地裂房屋倒,
堰塞湖上显茅排,
沟壑条条连尖峰,
坡岭弄场尽流泥,
五禽六畜死无数,
人殁漂浮满江堤。
各种野兽互打抢,
吃肉啃骨无完尸,
蚊蝇嗡嗡蛆滚动,
臭气难闻令呕窒,
惨不忍睹祸连片,
存活民者哀凄凄。
敢松珍凤惊胆寒,
目瞪口呆身颤栗,
沉思多遍渐清醒,
赧颜顿现头低垂,
经过点拨焕活力,
为爱奋发再搏击。
符华先:
眼见为真耳听虚,
实景入睑应认知,
万类生灵绝在即,
坐卧不安泪湿衣。
造物不易须珍惜,
岂能旁观坐待毙?
密阳洛陀话诚实,
应以理解勿猜疑,
孩们遭罪心烦乱,
多给安慰少斥之,
丢掉忧愁往前看,
焕发青春创奇迹。
同心协力寻宝剑,
剿灭魑魅志不移,
排除艰险平灾患,
拯救人类树旗帜。
敢松珍凤且住下,
前行与否再商议,
总有解决好办法,
不必着急伤和气。
敢松:
凡间苦痛多原因,
一言难尽不可忘,
妖怪作恶布毒瘴,
祸害下界实在狂,
宰除魍魉是责任,
解救民众理应当。
世间本以人作主,
岂容魑魅来兴浪?
男儿大志在四方,
敢将热血洒疆场,
披荆斩棘顶风去,
赴汤蹈火灭虎狼,
遵循旨意登弥兰,
取回神剑降魔王,
驱散雾岚净寰宇,
清风复吹喜气扬。
凤妹静心暂住此,
我自纵马独前往,
完成心愿即返回,
再择吉日进婚房。
珍凤:
双雄神剑分公母,
男女合力方取回,
郎君话语我赞成,
愿作伴侣携手去,
灾祸同担福分享,
生死与共不分离,
娘亲诺言千钧重,
一定兑现非儿戏。
生不逢时苦难多,
魂魄不安心憔悴,
带着牢铐明日走,
讴歌且舞道途怿,
自我约束克杂念,
遵规守纪志不移,
希求顺风又顺水,
凯旋而归再致礼。
假若半途遇不测,
恳请送尸凡间去,
与郎投胎同日生,
永远牵手长相依。
女引唱:
密本洛西走上前,
紧抱幺女喜泪滴,
柔声出语送祝福,
情深意切盼归来,
转身离去步沉稳,
人类有救心甚慰。
笑开尊口法华凤,
传授符法好慷慨,
武术拳击与刀剑,
棍杖矛戟皆传给,
避险口诀无一漏,
抑扬顿挫是经词,
登高飞翔施气功,
和盘托出不存私。
敢松珍凤刻苦练,
圣师教导牢牢记,
腾扬挪移惊飞鸟,
互相对打如仇敌,
起早贪黑汗如雨,
只求功夫精深奇:
手捏硬石成灰粉,
脚跺地陷深三尺,
口喷烈焰树烧焦,
升空疾驰如光逝,
虎豹目睹心恐惧,
猿猴远望叹莫及,
训练时间有月余,
各般武艺渐熟悉。
师傅临场看演练,
暗自高兴眼生辉,
多方检查细指点,
注意事项亦交代,
碧血宝剑送两把,
威力无比碰即死,
各自入鞘佩挂好,
抱拳致谢即离开。
山重水复弄深幽,
漫长征途多尘埃,
顺利与否未知数,
耐心翻卷看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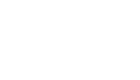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喜 鹊 之 歌
第二部《双雄神剑》
节选之三
困难重重
男引唱:
一夜无话悄悄过,
黎明来临便行动,
敢松念符召片云,
娘亲上坐皆踩空,
落在地面皮受伤,
连声哼叫甚苦痛,
不会轻功像石牛,
只得原地忍苦衷,
伐木加固篷四周,
拦挡野兽防吓恫,
反复交代莫吱声,
静静卧坐勿擅动,
安排就绪挥手别,
各自保重去匆匆。
恋侣相跟翩翩飞,
手脚如翼升苍穹,
直朝峰顶逐渐上,
快似鹞鹰胜飞鸿。
白雪皑皑脚下过,
日光反射耀双瞳,
展目四望各层面,
了解地形好操控,
刚到半山暴风起,
咆哮如雷轰隆隆,
震耳欲聋身受阻,
方向难辨何西东,
轻飘而下落坡底,
摔在地泥鼻脸肿,
稍微喘气揉揉胸,
携手急跑穿草丛,
欲到南面找静处,
躲灾避难少惊忪。
谁知树林叶梢颤,
左右颠摇似浪涌,
断折无数连根拔,
旋卷而去势汹汹。
脸色苍白俩神侣,
只得傍岩抑困窘,
天不作美心焦急,
能否复出待后咏。
女引唱:
长风旋舞呼啸急,
席卷大地过万嶂,
来得迅猛天地暗,
惊心动魄令心慌。
接近中午方止停,
满坡树竹皆遭殃,
吹走无数影不见,
抛撒何方难显彰,
空余山石光秃秃,
岭梁沉寂显瘦壤。
敢松珍凤现呆愣,
言语不得生惊恇,
赶往篷架所在区,
一片灰蒙不见娘,
逐个坡面慢搜寻,
查看幽谷上高岗,
走遍洼弄亦徒然,
皆无踪影甚渺茫。
敢松瘫软坐地泥,
昏厥多次特悲伤,
跪求天爷开鸿恩,
送母归来降吉祥,
或者示意某兆象,
冥冥之中指路向,
三拜九叩谢万遍,
当牛做马愿受杖,
珍凤悲泪流似雨,
默默陪伴无声响,
沉思许久才开腔,
语意特殊另别样,
示爱说真掏肺腑,
字字句句出衷肠。
珍凤:
哥哥苦楚原由多,
妹我深知忧忡忡,
接二连三出祸事,
惨不忍睹引号恸,
父亲英妹刚下葬,
母亲遭险又失踪,
生死未卜肝肺痛,
伤至骨髓如刀捅。
诸此种种好恼火,
皆因罗立乱操纵,
刁难我俩耍花样,
看似考验实布恐,
为爱奔命累荒野,
遭受掣肘灾重重,
虚度青春白费力,
及早清醒别懵懂。
实话披露吐心语,
请哥考虑求共同:
弥兰山上雪覆盖,
片石不见冰塞壅,
宝器有否存疑问,
当猴戏耍引笑哄。
痛定思痛想未来,
谋求出路去变通,
就近找个小村寨,
融入当地民众中,
搭棚居住随时势,
开荒自种食至终,
空则到此祭父母,
与妹闲聊说种种,
阴阳两界各独眠,
梦里相见情亦浓。 敢松:
凤妹话意可理解,
听之温暖合常识,
我也很想这么做,
自由自在心欢怡,
日出而作青山下,
动筋累骨无所谓,
野菜充饥亦高兴,
苦当娱乐磨志气,
夜与妻子对古歌,
怀抱孩儿双倚寐,
梦里同游百花园,
畅饮飞泉观峰巍,
翱翔太空看美景,
万里长空双比翼。
现实残酷多阴森,
事与愿违相脱离,
改变初衷躲僻壤,
建立小家忘众利,
千万灾民水火中,
心不安来魂亦哀,
密阳洛陀定严惩,
打入地牢变尘霾,
辜负始祖符华先,
死不瞑目悔莫及。
我俩教训太深刻,
无错也当有罪击,
整天烦忧被欺凌,
郁郁寡欢不得志,
现有机会应把握,
齐力拼搏而为之,
暂时收心罢痴想,
取出雄剑再商议。
男引唱:
句句在理撼心魄,
无言以对是珍凤,
过去遭遇甚凄惨,
苦痛彻骨如钉钉,
难以忘怀暂抑制,
服从大局独自撑。
敢松抹泪站起来,
拍其肩膀给鼓劲,
破涕为笑眼传情,
心事重重渐趋轻,
母亲之事虽棘手,
暂搁一旁待理清。
克己为民须先行,
暴雨过后自然晴,
不忘使命携手去,
胜利与否你点睛。
再次登山刚立足,
三只老雕从天降,
低空盘旋风呼呼,
扇起雪屑乱纷扬。
双翅长度约丈余,
灰白迷蒙硬似钢,
腿脚皮黄爪尖锐,
铁喙略勾像标枪,
体形硕大百多斤,
眼珠淡红隼般亮,
朝着情侣猛扑来,
欲叼撕吃极猖狂。
从未遇见此怪兽,
凶猛无比甚惊惶,
怎样应对方脱险,
拭目以待看下章。
男引唱:
鹰雕弱点众人知,
捕捉猎物倾全力,
空中望见垂直下,
很难改向抽身退。
这些特性敢松知,
抬头上看深回忆,
传授要点给珍凤,
牢记脑中作准备。
三只同时俯冲到,
胆小之人定吓死,
看得真切怒上心,
敢松珍凤各跳开,
距敌丈余闪两旁,
快如雷电似风疾,
双目圆睁瞄清楚,
迅速回手甚凌厉。
敢松剑锋对颈项,
快速劈落雕一只,
扑腾几下垂羽翼,
胡乱窜动倒雪地;
珍凤勇敢且机智,
凝劲等待静站立,
趁雕触地霎那时,
利刀挥去劲无比,
斩断双爪各纷飞,
老雕扑腾站不起,
闪电一般再猛砍,
脖子喷血身首离。
还有一只见此状,
慌张挪足欲反击,
敢松未待张翅膀,
猛地突刺捅后背,
尖刃入腔转把柄,
前进抽动插多次,
搅烂肝肺破胃肠,
畜生哀鸣力丧失,
闭住眼睛左右晃,
毙命而亡无声息,
喘过气来两情侣,
拥抱互吻心欢喜。
谁知乌云翻滚至,
越聚越浓叠层低,
张眼可见头上过,
阴霾沉沉罩大地,
正值中午晴空时,
奇怪现象却暌违,
两人对视脸惊骇,
何方妖精又来袭?
女引唱:
敢松珍凤仰头看,
满脸狐疑甚焦躁,
探讨原因话未完,
拳头样大冰雹到。
山上无物可遮身,
只得疾驰往南跑,
寻得小洞暂栖身,
任由天界撒花糕。
哔哔啪啪似爆竹,
刷过脚边声沨嚣,
大小不一弹跳去,
击入泥土成坑槽,
袋烟功夫方停止,
石上地面如白膏。
争分夺秒登峰顶,
立足未稳风狂啸,
似是奔马来万千,
震耳欲聋山颠摇,
惊心动魄胆寒颤,
普通恋侣怎逃脱?







喜 鹊 之 歌
第二部《双雄神剑》
节选之四
勇夺宝物
男引唱:
突如其来风再袭,
咆哮而过撼天地,
呼啸不断甚猛烈,
摧枯拉朽百物衰,
意念慌乱俩恋侣,
双眼难睁目迷离,
手足无措现呆愣,
张口结舌不胜悲。
身子随即轻如鸿,
不能自主脚移位,
左右摇晃寒意袭,
前后趔趄欲跌摔,
昏昏糊糊似衰竭,
往后退走好几尺。
危险二字闪脑际,
不约而同深呼吸,
施展气功立马桩,
平衡四肢抗暴力,
继而卧倒手牵手,
雪上并排肩相倚,
共同凝劲心一致,
出语坚定互激励。
雪粒冰块纷纷至,
击打全身似疾矢,
不断翻体防冷冻,
水珠串串滴淋漓。
久卧湿地渐颤抖,
哆嗦不已脸呈紫,
挺起胸膛速站立,
展开双臂去如飞,
朝着南面顺斜坡,
欲寻僻处暂避危,
谁知遇上强风口,
珍凤被卷下山陂,
飘飘忽忽落草丛,
死活不知多凄哀。
女引唱:
间隔丈余敢松见,
惊恐万状泪如滂,
连声呼喊好凄厉,
张开双臂速下降。
抱住恋侣摸鼻息,
捏住人中轻摇晃,
擦拭血口止外滴,
敷上药粉促早康。
慢动四肢看瘀点,
推拿摩挲查胸腔,
筋骨完好心稍安,
止住泣声渐息慌,
半个时辰悄然去,
珍凤醒来互致祥。
暴风远逝四野静,
艳阳复照天晴朗,
抬手动脚展臂膀,
劲力如初重整装,
相携腾翔并肩飞,
旋即又临弥兰冈。
男引唱:
落足峰顶速定位,
选择平台寻目标,
掏出囊中酒与纸,
摆上肉类及饼糕,
捡拾干柴引火绒①,
点燃香蜡烟缭绕。
灵犀相通急跪地,
摒弃杂念各默祷,
反复诵经请师傅,
躬迎圣母与耕杲,
亦拜山神和地公,
同来现场互关照。
三躬完毕即站起,
神色严肃显诚孝,
烧化冥币成灰烬,
慢浇水酒当酬报。
丈余之外有异响,
哔啪震裂痕多道,
霜花消融现铁盒,
雪白透亮胜月皎,
宽约一尺呈扁形,
双剑于内似龙蛟,
紧紧黏合分为二,
长短并齐如双胞,
阳光斜照闪金星,
耀眼夺目映九霄。
协力出刀破坚冰,
露出多半见花雕,
看准中点紧绑绳,
两根缠绕求牢靠。
聚劲拉起慢提升,
左右移动轻扶摇,
当啷一声离基座,
腾空直升丈多高。
————————
注释:
1火绒:古时布努人
用艾草或其他可
燃物沾硝粉做成的
点火物,有的地方
叫做火纸。
情势不好敢松急,
施展轻功抓索套,
双手配合往下拉,
企图稳住入怀抱。
谁知祸事又发生,
轰隆雪崩起狂涛,
呼啦作响滑坡去,
地动山摇似风啸,
趔趄后仰恋友晃,
卷入其间任旋飘。
珍凤惊叫速腾起,
随即跃下心忉忉,
初时看见爱人影,
眨眼消失无形貌,
往返多次雪上飞,
呼天喊地大嚎啕,
结局如何焦肝肺,
第三部书方揭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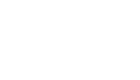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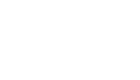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赵放岚(幽兰一箭香) :感谢世界文学艺术家协会给瑶族长篇爱情叙述诗展示的平台,感谢张主席、赵副主席的精心策划、编排,使长诗能锦上添花,悠扬传万里![强][强][合十][合十][合十][握手][握手]







编辑:赵放岚
图文:蓝朝云
视频:蓝朝云
李宏军
配乐:网 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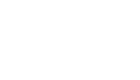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作者赵放岚,笔名幽兰一箭香。1949年10月11日出生于云南腾冲,祖籍湖南宁乡,中国远征军之后,共和国的同龄人。
小学就读于盈江县旧城完小。中学就读于腾冲县和顺益群中学。中学时代,赶上文化大革命,69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盈江十三团接受再教育十五年,后调到地方从教。在工作中,边教书边自修,先后在德宏教育学院修完中文专科,在云南师范学院修完中文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职称中学高级教师。担任盈江县第一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担任高中年级主任。在担任年级主任期间,2002届高考,率领全级师生刷新了盈江县的高考记录。
退休后定居昆明,先后在云南新华电脑学院和学大教育从教十一年。 在普通教育中,曾多次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工会工作者光荣称号并获得奖励。在云南新华电脑学院任教期间,参加2006年云南省首届“现代化教学及模块式课程改革成果”评选活动中,荣获省级二等奖。在学大教育任教期间,以学大教育专家身份,曾两次接受《昆明生活新报》记者采访,并在《昆明生活新报》发表对个性化教育的见解和本人的教育事迹。在学大教育期间,先后获得“最忠诚学大员工奖”、“学大全国教育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学大教育突出贡献奖”。
2018年2月,荣获“梦影回廊诗词歌赋总社”首届现代诗歌大赛“优秀作品奖”。
2018年,荣获上云诗社主办的“华文杯”首届华语童谣大赛“最佳人气奖”。
2019年元旦,在三年一度的世界文协第三届“吉春奖”评选中,由中国文缘出版的《赵放岚文集》中,世界文化名人吉春为之作序的《情诗一百首》荣获“吉春文学奖”,并因成绩优异荣获“特别贡献奖”。
2019年9月18日,荣获“三苏文学杯”银奖。
2019年12月发表在《中国当代诗歌新编》的《大观楼赏雨荷》荣获“当代诗歌优秀奖”。
2020年元月,荣获中国燕京文化集团评选的“中国梦的实现一一21世纪初炎黄诗坛领军人物”奖。同月,荣获中国燕京文化集团首届成立五大文学研究院中“中国诗歌百年发展传承研究院”首批院士称号。
2022年元月,《回忆录》一一《峥嵘岁月》,诗歌《咏兰诗组》,荣获第四庙“吉春文学奖”。
2020年12月,代表作诗歌《西山恋,滇池情》、《盈江恋》,散文代表作《樱花雨》、 《昆明湖畅想》、《古滇国遐想》发表在中国燕京文化集团,尹长磊主编的《万法归宗 当代诗坛 领袖代表人物作品录》。
2021年12月,诗歌《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发表在中国燕京文化集团 ,尹长磊主编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情怀 翰墨飘香》。
现在德江分会参加老协活动;任德江分会活动简报编辑;任盈江县老年人协会昆明分会活动报道编辑;任昆明官渡区延安精神研究会知青分会活动报道编辑;任昆明滇韵文体艺术研究会活动报道编辑;任云南红土地知青文化联谊会活动报道编辑;任理想科技集团代言人;任春城无处不飞花群群主兼活动报道编辑;任腾冲和顺益群中学昆明校友会活动报道编辑;任婧翊艺术团活动报道编辑;任世界文学艺 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昆明分会主席,《世界文协文学》副主编;任“三苏文学社”副社长;任北方文化艺术群活动宣传报道编辑;任龙风文学 院红二区直属一区1157分院教学活动宣传报道编辑;[幽兰一箭香文苑]群主;[幽兰一箭香诗社]社长、主编;幽兰一箭香温馨家园群主。
平时喜欢写点诗歌散文等。







人生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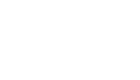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幽兰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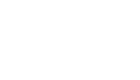

特别声明: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VV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Copyright © 1999-2017 世界经济合作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主办单位: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商业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分会/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咨询专家委员会
合作电话:010-83065260 稿件信箱:1486910993@qq.com 投诉邮箱:lixiaotian0927@126.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68号希尔顿酒店B座写字楼1119号楼上 企业微信SCRM
